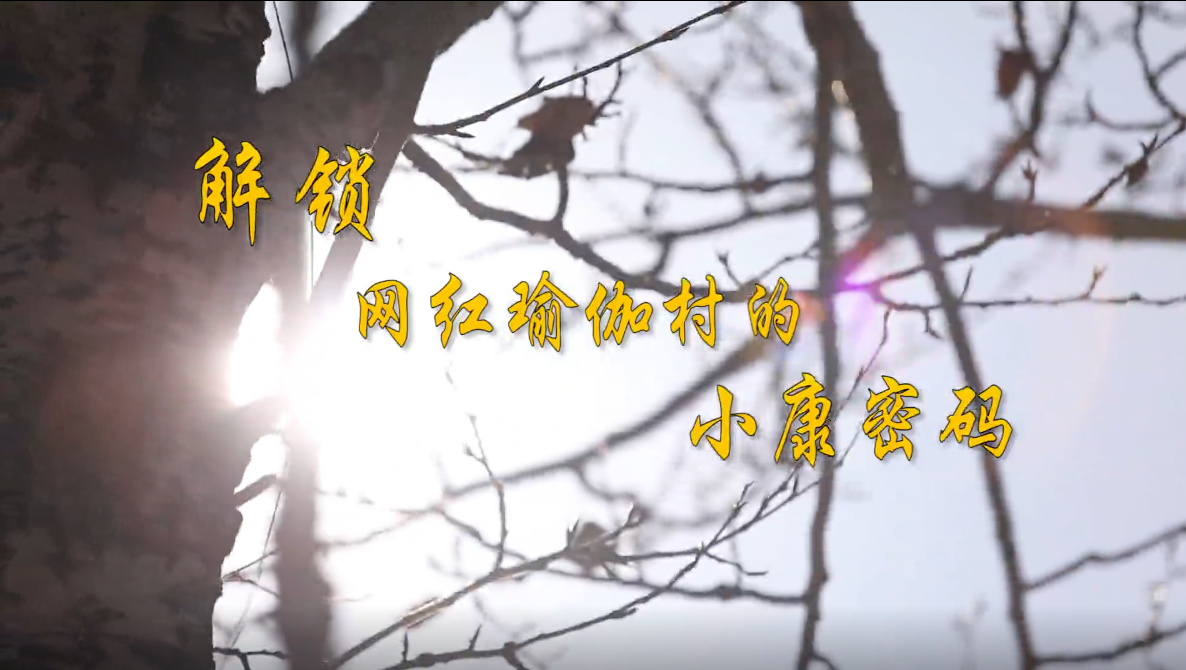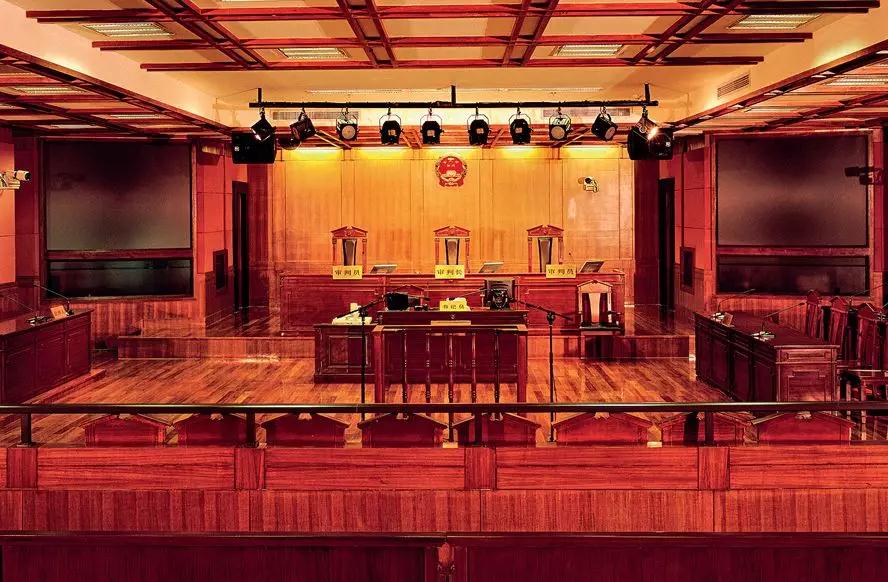张联弛:让折翼天使也能飞翔
孩子的降生就像是天使降临,带给一个家庭快乐,同时也享受生命的过程,但是,当孩子是智障,是脑瘫,是唐氏综合征……他们的人生该如何展开呢?哈尔滨市南岗区辽源学校校长张联弛说,折翼天使也是天使。她所有的努力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最普通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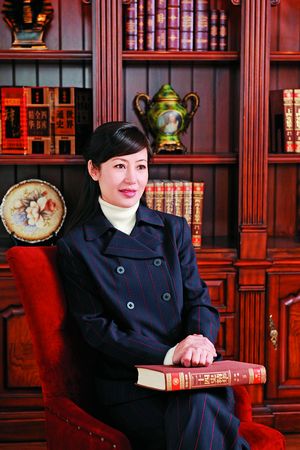
张联驰是国内首家“培智儿童康复指导中心”的创办者
一口吃下孩子勺子里的饭菜
清晨的阳光斜斜地铺进校园,哈尔滨市南岗区燎原学校的老师们年轻的面孔盈满笑意,站在校门口迎接他们的学生。
这是一群特殊的学生,大多表情呆滞,吐字含混,走起路来趔趔趄趄。但每个人都懂得向老师问好,声音很大,无邪的笑容令人心痛。
校长张联弛叫一个孩子的名字,问他:“我是谁?”孩子转头羞涩一笑:“你是老师……李老师。”
他又不记得她了。
但校长记得他。校长能讲出每一个学生背后一长串不幸的故事,也能讲出点滴让她心动的进步。谁是脑瘫,最初只能跳着走路,现在会跑了;谁是老师们最喜欢的“唐宝宝”(唐氏综合征),学会了洗衣做饭……说起他们的每一点成绩,她都有一种母亲夸耀孩子的骄傲。
早晨的升旗仪式和普通学校并无二致,两百多孩子列队站了一操场,他们显然训练有素,知道自己站队的位置。老师介绍升旗手,被夸赞的孩子偷偷笑着,得意非常。少先队员行队礼,一个患脑瘫的小男孩表情倔强严肃,他极力挺起胸膛,红领巾被白色运动衣衬得分外鲜艳,只是,他的胳膊,要靠老师抓扶着才能举起来。
中午,孩子们在教室里打开自带的饭盒,张联弛亲亲热热地查看大家的饭菜,叮嘱这个慢点吃,关照那个别只顾喝水,又提醒老师让吃饭“神速”的孩子下次带一把小点的勺子来。一个“唐宝宝”将一勺饭菜举到校长面前,声音含混:“老师吃。”张联弛毫不犹豫地低头一口吃下,乐呵呵地夸:“真好吃!”
燎原学校每个班两个班主任,张联弛安排他们从一年级一直要教到九年级毕业,九年的相处,让老师和孩子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感情。
学校有个患自闭症的男孩,人高马大,力大无穷,发脾气的时候,能把10厘米管径的上下水管全拽折,一巴掌能推倒卫生间所有的隔墙。东西掉了,天气不好……所有小小的因素都可能让他雷霆万钧。张联弛安排一个男老师带他,每天清早从家长手里接过孩子,这一天就要和孩子成为“连体人”,哪怕是上厕所。老师察言观色,孩子翻个白眼儿,就得设法把他往操场上带,“用投球跑步把他的不良情绪疏解出去。”老师经常会被学生撂倒,身上总有青紫——燎原学校的老师都有被学生咬、掐、打的经历,张联弛安慰他们,这是孩子的一种交流方式,是因为“喜欢”。那个自闭症孩子毕业后进了残联的托养中心,一天,男老师去看他,怕惊扰他,不敢轻易近前,远远站住,叫了一声学生的名字。孩子愣住了,停下来盯着他看——自闭症的孩子,原不会有这个反应。老师慢慢张开双臂,像在学校里一样说,抱抱!孩子看着老师的眼睛,一点一点挪过去,一米九的大个子,就那样把老师裹进了怀里。这样的“待遇”,是连妈妈都得不到的。
孩子,总是能给人惊喜
与同区几所气派的学校相比,燎原学校的外表极尽简朴。然而,走进教学楼,小小五层却容纳了85间教室,其中功能性教室就有31间,多感官训练室、情绪宣泄室、脑瘫治疗室、音乐治疗室、缝纫室、餐饮实习室……一应俱全。许多设备是校长张联弛亲自设计,然后由老师们自制的。材料有汽油桶、旧轮胎、旧楼梯栏杆……重新打磨刷漆组装,大家评价“很好用”。
将医疗康复介入教学,并且不分主次,是张联弛的教学理念。
当年,张联弛是医院康复科的医生,接触到很多脑瘫孩子,“看孩子和看老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老人毕竟已经经历过人生,可孩子如果不能康复,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享受正常人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脑瘫孩子的康复。”
她认识了燎原学校的老校长,第一次来到这个学校。下课了,别的孩子都在玩闹,一个小女孩却蹲在一旁玩沙子。小小的孤独的身影触动了她,她走过去问,你怎么不跟同学们去玩啊?孩子不说话,把头扭过去。老师说,孩子是轻度脑瘫,智商正常,只是从不和人主动交流。在这个群体里也无法有正常的交流与沟通,她觉得她不属于这里,但她无处可去。
张联弛的心很疼,孩子出生已经受到过一次伤害,因为环境,她再次受伤。“如果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一定用我的康复知识帮助她,让她的肢体康复,变成一个正常孩子。”
2001年,她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在学校做了一名校医,开始将康复理念引入教学。
那个孩子叫丽丽,走路左脚绊右脚,身体无法载重,拿任何东西都会让她摔倒。手是僵硬的,还有语言障碍,妈妈说,她是个特别缠人的孩子。
孩子语言发展的最佳阶段是3到6岁,运动发展的最佳阶段是6到12岁,可是丽丽13岁了。张联弛想看孩子的脑CT片子和曾经的诊疗结果,家长拖了二十多天才带来,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还有救。
丽丽手部精细动作不好,需要激活小肌肉群的敏感度,张联弛将医院的冷热刺激疗法改良,先把丽丽的手放进冰水里,再迅速把煮热的鸡蛋在她手上反复摩擦抓握,保证疗效,也保证孩子的安全;丽丽的手指张不开,张联弛给丽丽编了手指操,又用白胶布把笔缠得粗粗的,让她能握住,慢慢学习笔画,再随着孩子的进步,把胶布一层层剥脱;丽丽的上肢定位能力差,张联弛就让老师在写字纸上打四个大方格,让她把字写进格子里,一年半以后,格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多,丽丽能在普通的田字格里写字了;丽丽还学会了摆扑克、玩电脑游戏,妈妈惊喜地发现,孩子不缠人了,会自己玩了……
丽丽今年已经23岁,姐姐开了一个复印社,丽丽会在电脑上帮姐姐打材料,虽然是“二指禅”,速度却很快。她在屏幕上敲下自己想说的话,在网络世界,她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孩子,总是能给人惊喜!在丽丽康复的同时,张联弛对两个脑瘫孩子也以纯医学的手段进行干预,仅仅半年,孩子就由不能站立到能站立几分钟。张联弛大受鼓舞,她的校医身份很快结束,从主任、副校长,直至校长,医教结合的方式在全校推广。

燎原学校的孩子是特奥会上的夺金大户
学不会乘除法,也能做健康人
燎原学校的每个教室都有一个电子白板,这是胡锦涛总书记送给孩子们的礼物。白板上显示着这节课各个年级不同的学习内容,有的在认识钟表,有的在学习如何自我介绍,有的在学如何画对角线。洗衣教室的孩子正弯腰在一个水盆里学洗头,职业高中班的孩子则在烹饪室一遍遍练习切菜和炒菜。进行一对一康复训练的孩子用僵硬的手指勉力捏起一个塑料片,在老师的鼓励声中将它们插成花朵……
那一年,张联弛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言语听觉科学系的黄昭鸣教授,借助于黄教授团队的专业知识,张联弛在学校进行实践,学校也成为黄教授的一个实验基地。
孩子的进步让家长吃惊,也让老师吃惊。曾经,他们认为自己对这些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只要不出事就好。突然有一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职业价值,平生第一次,做起了教材编写和课题研究的工作。围绕“让智障孩子能生存会生活”的教学目标,张联弛组织老师们编写“生活化课程”。“我们将正常人从有记忆开始所必需的生活能力,作为教材内容选择的横轴,纵轴则是从早上起来到晚上入睡,一天当中所必须做的事。学会这些,孩子们的生活就能自理。”
孩子的降生在任何一个家庭都像是天使降临,但小阳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折翼。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却要天天面对一个智障孩子,悲伤笼罩了全家,就连周围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个儿子。
小阳进了燎原学校,缓慢的进步让父母一天天绝望,在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干脆把小阳交给了爷爷奶奶,连家长会都不参加了。只有张联弛和老师们确信,小阳固然学不会乘除法,但小阳一样能做健康人。
有一年,小阳的父母回家陪老人过年,突然发现,小阳是同辈中最孝顺最听话最会照顾老人的孩子。这才知道,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小阳包下来了所有的家务事,还负责老人的一日三餐——早晨起来把早饭和午饭都做出来,下午放学再赶回去做晚饭,只要从学校学了新菜,必定回家演练。父母惊喜万分,抱着小阳左看右看,像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儿子。小阳被接回到父母身边,终于能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
张联弛很欣慰,“折翼天使,也是天使。”
2009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到燎原学校视察,深情地说: “你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用自己的爱心和奉献帮助孩子们成长进步,我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说完,向老师们深深鞠躬……

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老师们快乐的理由
教育孩子,也教育家长
放学了,一群家长忧戚地等在校门口。隔壁中学的操场传来阵阵欢笑,家长们却一片静默。孩子们出来了,有一个认出了记者,突然大叫一声“客人见!”他其实是想说,客人再见。家长急匆匆地从老师手里接过孩子,很快消失在马路上。
燎原学校的老师很容易遭遇“难缠”的家长,张联弛说,一个家庭有了这样的孩子,无论事业多么成功,家长都永远不会有彻头彻尾的快乐了,孩子是压在他们心里一辈子的石头,他们情绪不正常是应该得到理解的。
其实,孩子才是负面情绪的直接受害者。
常征一岁的时候特别能哭闹,对妈妈来和妈妈走都没有感觉,眼神永远游离。仿佛常征只是身体降临到了这个世界,灵魂却不知迷路在哪里。三岁,他被确诊为自闭症。
常征刚到燎原学校的时候,程度并不十分严重,只是有轻微的自虐行为。但很快,孩子变得越来越暴力,经常对戴眼镜的老师发起攻击,发起脾气来,能把饮水机从楼上扔下去,几个老师都抱不住。还冲进超市抢饮料喝,抓起瓶子先揭开盖子甩出去,然后飞快地喝一口,得意地四下看看,表示了自己对这瓶饮料的占有。张联弛研究常征这一系列行为,认为孩子“存在家庭养护障碍问题,他是在模仿”。“冲进去抢东西说明平时孩子对东西有欲望的时候家长不满足,他就用抢的方式解决;迅速把盖子拧开扔掉,说明家长有过这个动作,比如他抢来的东西被家长夺回去扔掉……”
去家访,常征的妈妈痛哭失声。孩子的病让夫妻俩彻底崩溃,两人关系严重恶化。爸爸选择逃避,早出晚归,尽量不和孩子发生交集,心力交瘁的妈妈只好把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但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开始反抗,而妈妈的眼镜总是他先攻击的目标……
常征的表现,让张联弛注意到家校结合的重要。张联弛说,学校老师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教学生,百分之四十的精力在教家长。老师通过家长会,通过家校练习本,通过各种途径,告诉家长很多特教和医学的方法。
哈尔滨天黑得早,送走学生,太阳已经西斜,这群平均年龄只有31岁的老师亲热得像一家人,围在他们的“张姐”身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某某会上楼了,某某懂得幽默了……言辞风趣,让张联弛一次次笑弯了腰,她说,我们学校是培养人幸福感的地方,我们的老师们都特别容易知足!■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