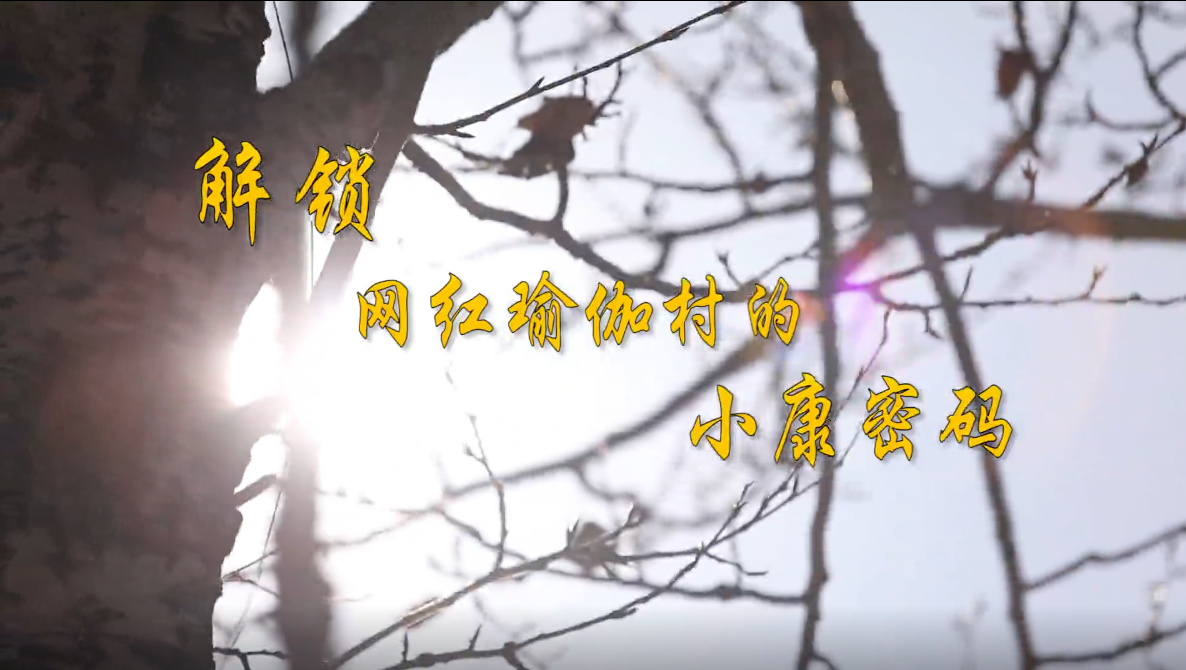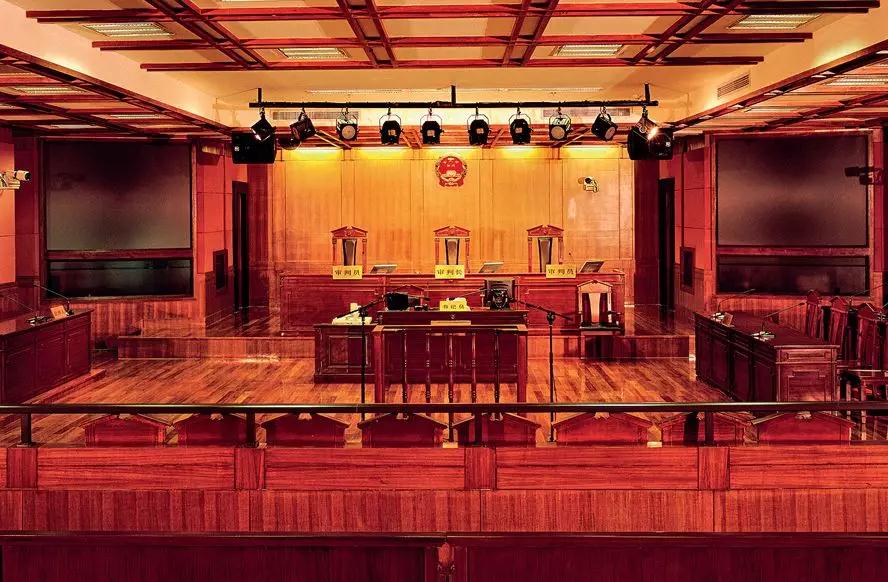京剧新偶像王珮瑜
天赋是会被用完的
刚刚在北大、清华掀起了京剧偶像热浪的“小冬皇”王珮瑜,又走进梅兰芳大剧院,演出传统老戏《桑园寄子》和《琼林宴》。
在与戏迷的见面会上,王珮瑜说:“我觉得自己有很好的当导演或制作人的天赋,如果有一天退居幕后了,我会做一个掌握全局的人。”
其实早在八年前,王珮瑜就想当一个掌握全局的人,那时,年仅25岁的她已经是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副团长,在事业的巅峰时刻,她突然宣布辞职,不顾周围人阻拦,下海开了个人京剧工作室。
25岁以前,王珮瑜的人生道路铺满鲜花。她的舅舅是票友,将她领入京剧大门,她开蒙学的是老旦,几个月后以一出《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一次去广播电台录音,一位老先生告诉她:她的天赋虽好,但唱老旦却永远不能挂头牌,应该去唱老生。王珮瑜立刻被“挂头牌”三个字吸引,1992年,她考入上海市戏曲学校专攻老生行当。她熟唱余叔岩先生留下来的十八张半唱片,在各种少儿京剧比赛中过关斩将,16岁时以一折《文昭关》技惊四座,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惊叹道:“这不就是当年的孟小冬吗?”从此,“小孟小冬”声名在外。
为了提携这位后辈,70岁高龄的谭元寿亲自为她献花,更主动与她合演《失空斩》。1993年,她又得以跟梅葆玖先生同台,临时顶替梅葆玥演《文昭关》。演完后,梅葆玖赞叹“太意外了”。之后,把她的名字带到了北京,逢人就说上海有个王珮瑜。以至于她后来去北京演出,一报名字,人家就说,噢,就是梅葆玖说的那个演员。
王珮瑜是作为“特殊人才”被上海京剧院引进的,院方一次性给予15万元的安家费奖励。彼时,王珮瑜在京剧圈内早已名噪一时,“七八十岁的前辈见到我也叫瑜老板,现在想想很汗颜,当时却觉得很自然。”
作为上海京剧院最年轻的副团长,王珮瑜全面负责剧团的人才培养、演出、剧目建设。那一年,她试图大胆改革,提出以人为本,要给跑龙套的人多发钱,主张有什么人排什么戏,打破以往先有戏再找人的套路……改革推行得并不顺利,有人说她打破了游戏规则,还有人怪她把剧团搞得“鸡飞狗跳”。
骄傲的王珮瑜看不起所有发出反对声音的人,她无法忍受再待在这个“腐朽”的行业里,决定自己去做一番事情。
王珮瑜扔掉“铁饭碗”的事引来社会关注,媒体以《王珮瑜辞了团长干“个体”,挣脱旧体制不走回头路》为题报道了她的故事。有记者问她,如果市场运营不成功,你会回到上海京剧院吗?她回答:我的市场运营成功与否,都不是我回到原点的理由。记者又问,你有“后台”吗?她自信满满:我的后台是市场,是自信,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声……
多年以后,她这样总结自己的一意孤行:“那时的我少年得志,自我膨胀,突然辞职是过往所有顺利饱和后的一个状态,好像必须要做一些破坏,以表现自己有能力。”那时的她是靠天赋在立足,她要在经历过挫折之后才能明白,天赋是会用完的,真正能成功的人,绝不是靠天赋走到最后。
个人不过沧海一粟
2004年,单飞的王珮瑜心情很好,她以为摆脱了体制的羁绊,可以多唱戏了。没想到,很快就迎来了考验:演出机会不稳定,利润小,工作室难以为继。当时的固定人员只有化妆师、鼓师、琴师和主要配角。每一场演出,得向体制内的剧院借服装、借道具、借演员,全要仰人鼻息。而且原先剧团几十人干的活,现在都压在王珮瑜一个人身上:订机票、谈生意、算账、约演员、缴电话费、签法律文书、排演出日程……这才发现,“京剧是一件集体协作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她用“像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小东西”来形容那时的孤独与无助。而最让她沮丧的是,越来越没戏唱了。
市场没有成为她的“后台”,还吃掉了她几年的积蓄。“我四处碰壁,受了很多委屈很多苦,终于知道了什么叫苦涩,我开始整宿整宿失眠。如果继续走下去,就一路错到底,如果回来,我这张脸往哪里搁?骑虎难下了。”
最终,铩羽而归的王珮瑜还是不得不放下身段回到了上海京剧院。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可王珮瑜说,“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必须得回来。一滴水容易干涸,唯一的出路是把自己融进大江大海里。”
剧院虽然欢迎她回来,但物是人非,她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风光,副团长有人替代了,专业上的位置也有了新人。事实证明,京剧院不会因为王珮瑜走了而开不了戏,但王珮瑜没有了京剧院这个舞台,是唱不了戏的。她第一次懂得了“谦卑”两个字的含义,“突然觉得自己成熟了。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因为观众很快会忘记我的,我要赶紧唱戏赶紧学戏。”
她用打造个人品牌的方式来救自己。她在上海京剧院办了个“京剧跟我学”的普及班,亲自做公开课,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小资、白领成了她的戏迷,还有老外来参与。她出唱片、出书、开讲座、上电视……扩大自己名声的同时,也实现个人品牌商业价值的最大化。王珮瑜给自己的新定位是“做最古老的传统艺术中最时尚的演绎者”。
2010年,王珮瑜在天津和北京演出了墨壳原态舞台剧《乌盆记》,将相声、评书、 京剧三种艺术形式溶于一炉,有单田芳说书,马志明跟黄族民的传统相声段子,整部戏用最原生态的表演方式与观众见面,连宣传海报用的都是旧戏报,观众认可度极高,在京津两地一票难求;她推出的京剧与吉他的创意音乐组合,为她在网上赢得超高人气;她亲自参与制作的兼取马(连良)、余(叔岩)两派之美的墨本丹青版《赵氏孤儿》,在沪上取得了票房飘红的成绩后,又助她荣膺第25届戏剧“梅花奖”。
对传统艺术有了新的理解,同时对市场有了更深刻洞察力的王珮瑜,重新成为新京剧偶像,只是,她的表情里再也没有轻狂与得意,言谈举止透出的是谦恭与笃定。过去,她把那段下海经历称为“走了一段弯路”,而今,她说:“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我并不后悔走过那个所谓的弯路,所有的坎坷都是必须要经历的。30岁之后,知道了天高地厚,为人要更从容,要有更大的心胸,更大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