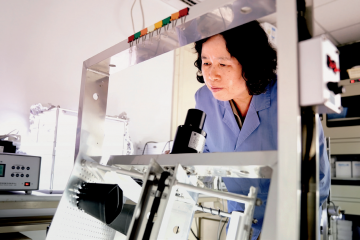李少红:世妇会让我有了性别自觉
30年前,李少红作为中国电影界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次经历让她首次直面性别议题的全球语境,意识到女性视角的独特价值——“性别差异不应是限制,而应成为创作的自觉优势。”
30年后回望,李少红最难忘的情景,是当时外国记者反复追问“中国有多少女导演”,她惊讶之余回答“仅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有20多位”。北京世妇会后,李少红的艺术轨迹与这场大会的精神共振愈发清晰,她的镜头语言始终与“以行动谋求平等”的世妇会精神同频,她的创作从此有了独到的性别自觉与时代使命。

用女性视角讲故事
1995年,是李少红导演生涯中难忘且重要的一年。她凭借《红粉》获得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也是在那一年,她作为中国女导演的代表参加了北京世妇会。“生活在妇女解放的中国,我惊讶于世妇会对妇女的重视,原来还有一些国家的女性没有选举权,这使我大受震撼。”
李少红笑说自己当年还是青年导演,《红粉》拍摄时坚持采用女性视角被很多人反对,这使她怀疑自己的视角是不是太狭隘了,但她一直有一种朦胧的意识,觉得自己就应该从女性角度讲故事,所以她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主张。参加世妇会后,她才知道,正是自己的性别意识才使得《红粉》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
在《红粉》之前,李少红拍摄的《银蛇谋杀案》《血色清晨》被人评价为“凶猛异常”,还得了个“女人比男人更凶残”的外号,她曾为这种模糊了性别的评价而高兴,但在内心深处,她一直隐隐感到不适却又无法言说,直到在世妇会上,李少红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清晰的认识后,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她说,“如果说拍《红粉》的时候,我是懵懂的,只是跟着直觉采用女性视角进行叙事,那么世妇会则是打开我创作领域的分水岭。在世妇会之前,我很不喜欢被别人强调女导演这个身份,后来我不再回避性别,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男女共存的世界,不能只有男性的声音,女性也要有自己的声音,也需要被看见。”
如今,提到李少红,人们会说起她的经典作品《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生死劫》,会谈论她细腻又鲜明的独特风格,会冠之以“优秀的女性电影人”身份,但这些都不足以描绘李少红。
1978年,李少红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成为同学。大学毕业后,陈凯歌在筹划《黄土地》,张艺谋决定拍《一个和八个》,田壮壮计划拍摄《盗马贼》,大家围在一起热火朝天地改剧本,而李少红眼下要“探讨”的是和丈夫意外有了一个小生命。她从未掩藏过自己的野心,只是她更明白厚积薄发的含义,所以选择顺从内心,调整人生经历的顺序。
女儿的出生令李少红对生命的珍贵、女性的坚韧有了更深的理解,得知陈凯歌等人的电影获奖时,她为他们高兴,但也切肤般感受到女性的母职困境。“后来大家的电影拍完了,都得奖了,只有我还停留在原地,会有些委屈,但是我孕育的生命也是一件作品。因为我小时候得到母亲的陪伴很少,所以我决定不给女儿留下遗憾,等她上幼儿园了,再开启我的事业。”说这些话时,李少红温柔而坚定,她从内心里觉得做母亲和做其他工作没什么区别,所以在多年后,有人再次问她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时,她坦然地回答:“每年都有记者问类似的问题,我很好奇为什么不问男导演?”
李少红的变化正如她女儿申申所说:“最开始她觉得女人做导演可能会狭隘,她想活成一个男人,所以表达非常尖锐,到后来她觉醒的女性视角很强烈,换了一种姿势和世界搏斗。现在她平和了很多,就像《大明宫词》,我看了好几遍才明白她想表达什么,其实她想说的是,女人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优秀而成为一个男人,而是应该真正认同并赞美自己是一个女人。”
一家三代女性的电影梦
《大明宫词》里的武则天是一个帝国的管理者,也是一个深爱女儿的母亲,更是一个会脆弱会寂寞的女人。在描述此剧的拍摄过程时,李少红提到了“想象”二字,她说:“武则天的碑是无字碑,太平公主在史料中的记载极少,要把历史上的女性故事讲出来,需要想象,也需要我站在女性的角度还原这些不被看见的女性的生活。武则天既是妻子、母亲,又是女儿,要想象她的生活中存在哪些关系。”母女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君臣关系,让剧中所有人物都变得有血有肉,李少红通过重新解构,赋予了女性历史人物新的生命,将历史与艺术结合在一起,从女性本位视角再现了女性形象。

说到自己的母亲,李少红笑了起来:“我妈妈很有个性,她是文工团的,会唱美声,本有机会去外语学院学外语,但她非要学电影。她当时拍的片子非常个性化,所以我觉得电影是一种基因传承,传承到我身上,也是希望能够创新,对艺术表现有极致的追求。”受到母亲的影响,李少红一直很有创造力和勇气,她敢于挑战新鲜事物,是电影导演里第一批用电脑写剧本的人、第一批拍电视剧的人。拍电视剧时又是最早一批接触数字化拍摄的人,在电影从胶片转型到数字化时,很多人转不过来,经历过电视剧数字化转型的她没有任何障碍。如今AI迅猛发展,她也要接触尝试一下,总结AI科技的优点与弊端。
作为母亲,李少红从不是大家长式的形象,她一直感谢女儿带给她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份体验又给了她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养分。在拍《橘子红了》秀禾怀孕的场景时,李少红希望周迅哭出来,但周迅认为没必要,两人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李少红试图让周迅理解女人孕育生命的喜悦,但周迅认为秀禾不爱老爷,这个孩子带给她的只有恐惧和厌恶,没有理由喜悦和激动。
“拍秀禾怀孕那场戏的时候是大年三十,大家都归心似箭,一直争执不下,我就说先过年,过完年后再拍。”到了大年初三,周迅给李少红打电话,说自己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了。原来她去郊外散心找感觉时,看到早春二月在田地里生长的幼苗,一下子就懂了女性独有的孕育生命的强大和爱。
谈到女儿,李少红的语气变得轻柔,她心疼女儿从时尚界跨界电影制片的艰难,也肯定女儿因为在剧组长大想要追逐电影梦的决心。“我觉得年轻人压力很大,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市场选择很残酷,我女儿的日常是上半夜跟统筹算时间,下半夜跟会计算钱,白天还要协调导演的艺术追求和市场的规则,协调剧组每个人每件事,她真的站着都能睡着。”她与女儿更像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朋友,母女两人因为热爱都在电影的世界里探索。
经历了电影技术的不断革新及市场的激烈竞争,李少红清楚地认识到,女性观众的增多是利与弊同在的,一方面,女性开始认同自己的性别,不再被传统观念束缚;但另一方面,女性容易被市场标签化,消费品化。她自己的感受是,不管媒体和市场怎么夸赞她的女性意识,在利益冲突时,女导演依旧变成被审视的第二性。
李少红的清醒里带着一种悲观,但她如水般的顽强和柔韧,让她将对女儿的爱和关心延伸到扶持青年女导演上。“社会上必须有更多女性导演,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声音,为女性导演争取更多的机会是我的责任。”
做女导演是一种享受

今年步入70岁的李少红状态年轻得令人难以相信,她喜欢真实用户活跃度高的社交软件,对一些大热爆款保持警惕,常常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自己吃到或者动手做的美食。她不会像个长者一样下权威的定义,而是告诉人们“没有对错”。她说起一家人都是搞电影的,都有强迫症,在家里因为电影拍摄事务较劲,谁也不让谁的故事时可爱地叹了口气,那是对艺术高度追求的幸福之叹。
如今,她依然对追求的东西不妥协,“有时候命里有东西等着你,如果你妥协了可能就没有了”,她说这句话时眼睛里闪着少女般澄明清澈的光;她和很多AI产品对话,和我们探讨AI与人脑的差异;为了弄清楚AI能够做哪些事,是否可以取代导演的工作,她问AI很多问题。在记者惊叹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之高时,她笑着回忆起自己拆摄像机的往事。她用很平淡的语气讲到自己是第一批被网暴的人,但她依旧愿意说出自己真实的体会和看法,她知道人言可畏,但她不会放弃表达自己,这是李少红式的澄明与珍贵。
采访中,李少红坐在软塌塌的导演椅中,温和平静地倾听,言语和蔼地交谈,时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声。她像是水,不是奔腾喧闹的溪流,而是波澜壮阔的大海。但她身上始终带着一种少女的锐气和少年的叛逆,像武侠剧中年少时风风火火、无所畏惧闯荡江湖,跌跌撞撞追寻理想,经历一番浮沉后,找到自己并开宗立派的大侠——温柔似水和侠气英姿在一个人身上如此鲜明地呈现,既有历经世事的沉稳,又有坚持自我的锋芒,一如大海浩瀚无涯,包容百川,却于远离陆地之处建构自己的岛屿,在纷繁复杂的世俗事务中葆有真实和理智。
采访尾声,李少红谈起拍摄《大明宫词》时,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在宗祠里18分钟的一镜到底的戏份,她仿若回到了27年前的拍摄当天,作为导演统筹全场,大家精心设计动作,不断修改,现场有8个调度,武则天的台词很长,需要一边祭拜祖宗,一边和太平公主说话,宗祠里光线很暗,大家的设备也不先进,执行导演因为害怕演员忘词直接趴在地上做“提词器”。等到大家悬着心听演员说完台词中的最后一个字,执行导演从地上爬起来欢呼,在场所有人都泪流满面。李少红说:“作为演员或者导演,你会享受那个时刻——剧组所有人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想要的表演效果那么微妙地活生生地没有丝毫误差地呈现出来了,这是多么感人的事!”
当被问到是否怀念那个技术落后但真诚炽热的年代时,李少红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真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