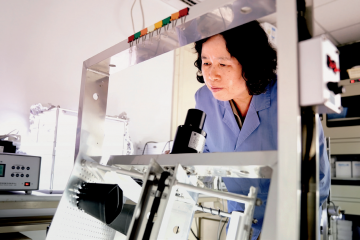梁子:最勇敢的“异文化冒险家”
9月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同一天“中非携手行动,教育赋能女性”中非妇女教育主题会议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彭丽媛在致辞中特别提到“中非女性用勤劳、智慧、奉献谱写了团结合作、携手前行的华丽篇章”。

梁子 中国第一位独自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获评中国电视学会年度最佳电视纪录片大奖(金奖),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赛人文社会类金奖,中国艺术摄影学会摄影金路奖,第五届 FIAP世界摄影大会“丝路风情与‘世界遗产’国际影像艺术大展”金像奖等。出版图书《红海大漠》《我的非洲部落》《非洲十年》等
到遥远的地方,把行走作为生活方式,并以文字和影像记录,在一点一滴改变自己心灵与胸怀的同时,也感染着更多人。这就是梁子,以行万里路的方式带我们读万卷书。
梁子:第一次去就觉得只要是非洲就行,一个台湾朋友介绍我去莱索托,海拔3000米的高原,但发现这个非洲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太冷了,厚衣服都没带,天天披着当地人的毛毯。
不行,不够典型,还得去。后来认识一个朋友在西非,我先问了一下情况,他说热死了。正好!我就去了塞拉利昂,赶上了十年“血腥钻石”之战尾声,人们从灌木丛林里陆续返回家园,生活很无序。
再然后一个朋友介绍我去海边,厄立特里亚,说有小木屋,我以为很浪漫,没想到最苦,三面沙漠一面海,一年只下两次雨,小木屋全是木板钉的。
第四次我专门选雨季去了一个雨水特别丰沛的地方——喀麦隆的林贝,年降水量排名世界第二。我待了两个多月,每天都是哗啦哗啦的雨,但是人们照样坐在树下聊天,没人打伞,以至于我现在下雨天都不爱带伞……就这样,去的地方越来越多。

阳光与石头灶,母亲与小儿子,食物与木板房,这就是东非阿法尔女人每天的生活状况(2003年摄)
《中国妇女》:到现在您已经去过20多次非洲了,但第一次去非洲时您甚至不会说英语,真的没有紧张过吗?在路上最有吸引力的事情是什么?
梁子:我第一次去非洲是2000年7月,感觉机场所有人都会说英语,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还是有点自卑的。从新加坡到南非转机是凌晨1点多,广播里的通知我听不懂,登机牌也不大看得懂,再加上时间特别紧,心里没底儿。后来我就专跟着黑人走,进了一个特深的通道(现在想其实就是廊桥),把登机牌给空中小姐一看,还真对了。
第二次是先飞阿姆斯特丹,再到加纳转机飞塞拉利昂。前一天晚上降落加纳,差不多要停留20多个小时才能接着飞。加纳的机场很小,不可能在里面等,怎么办呢?
在阿姆斯特丹排队登机时我就一直往身后看,全是外国人。快到我的时候,队尾突然出现了一个东方面孔,我立刻跑过去,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搭话,结果对方用普通话问我,你是中国人吧?原来是在加纳工作的北京人,亲人啊!聊起来竟然在北京有好几个共同认识的朋友,我就请他在加纳帮我介绍一个宾馆。
一出机场他去找车,我就被七八个黑人包围了,扑在我的行李上抢生意,幸好他及时解围,带我住到了中国医药总公司驻西非代表陈医生的家。陈医生也当过兵,大家喝酒聊天很投缘,后来的很多麻烦都是陈医生帮我解决的,甚至还帮我治过疟疾。
在路上,陌生人会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反复遇见。2001年我在加纳转机去塞拉利昂,和我一起下飞机的两个意大利人碰巧跟我住同一家宾馆,晚上其中一个人上吐下泻,敲我的门,我给了他黄连素,第二天早上这个人病好了,两人非要请我吃饭。
再以后他们回意大利,我在加纳乡下待了5个月,返回加纳首都准备从那里回国,当晚,一位朋友请我在一个黎巴嫩人开的餐厅吃饭,忽然就见那两个意大利人进来了,原来他们正好有事要办,也是当天才到。大家激动地拥抱。三年后我到意大利,其中一个人开车接我到他位于阿尔卑斯山下的家住了4天。类似这种陌生人变朋友的事儿实在太多了。
 特瓦族妇女靠捏泥罐谋生,在劳动中的欢歌笑语,远比卖泥罐挣钱更开心。(2007年摄)
特瓦族妇女靠捏泥罐谋生,在劳动中的欢歌笑语,远比卖泥罐挣钱更开心。(2007年摄)
《中国妇女》:您去非洲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住上几个月,这个时间是如何计划的?什么时候您会知道自己可以离开了?
梁子:其实第一次去非洲,计划住两年,我跟接纳我的大酋长说,我要去最原始自然的地方,他就介绍我去了他老家。太苦了,后来真的是待不住离开了。
有时候是当地人挽留,他们说,子,你别走,旱季结束马上就能看到芒果树结芒果,雨季还有捕鱼……这样就待了5个多月。
还有一次我本来打算9月回国,但听说10月18日一对结婚8年的夫妻因为生不出孩子要补办一次传统婚礼,就留下了。
我想婚礼当然是喜庆浪漫的,没想到他们却在婚礼上用杀牛宰羊的方式来祈愿。牛代表新郎,羊代表新娘,杀牛用的时间越长,难度越大,说明牛的生命力越顽强,预示新郎更强悍。
场面十分残酷血腥,一群人还敲着锅碗瓢盆声嘶力竭高唱“火木呀大爹”,“火木”是牛的意思,“大爹”是“先生”的尊称。血腥的歌声在这个七座山包围的乡村回荡,我一下蒙了,眼望群山,突然会问自己在哪里?为何而来?只有我一个异族人,孤独无助,无人共鸣。那一刻我无比想念中国。
《中国妇女》:您曾去探秘喀布尔的女性监狱,拍摄阿富汗的寡妇们,而且多年后会重访那些人,您关注女性,不只关注某个时刻的状态,而是更关注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的命运。
梁子:因为我是女性,和女性沟通更方便,甚至可以以交换女人隐私的方式来了解她们。
我采访一个人,喜欢展示个人生活成长轨迹跟国家民族命运的融会交错。我采访过三个阿富汗女性,一个是为女人制造美丽和快乐的美发沙龙老板;一个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寡妇,要靠辛苦烤馕养活一大家人;另一个是秉承“不许把悲伤带进家”的知识女性,她是家庭太阳能组装照明公司的技术骨干,战争导致她生了一个脑瘫孩子。
和真实的人打交道,每时每刻都是变化的,你无法预测她人生的走向,比如仅仅几年,开沙龙的不能开了,烤馕的瑞拉得了脑瘤,无法再烤馕,我都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在人间。
这个过程对我的意义非常大,影响着我的人生、眼界和胸怀。比如过去我锋芒毕露,非黑即白,做事完全按自己的喜好,后来会慢慢变柔软,变宽容,理解每个人成为现在的样子都是有渊源的。
《中国妇女》:您去非洲特别善于找组织,比如在喀麦隆采访一个“大工棚”的时候遇到阻力,就去求助当地妇联,得到了妇联主任的热情帮助,是吗?
梁子:我第一次去喀麦隆是因为河北石家庄办了个非洲妇女班,让我去讲课。我看到花名册里有喀麦隆人,就试着发了封邮件。对方回复说她的所在地是个省会城市,根据我的要求,她帮我对接了下一级的妇联组织。
这些妇联组织的领导一般是兼职,本身是某个行业的女能人,会帮妇女处理家暴,也开会做培训。妇女主任带我去村长家,通知妇女们10点开会,结果到12点都没来一个人。这是她们的常态。第二次弄了两箱啤酒,这下女人们都来了,二话不说,进门就喝酒跳舞,音乐声开得特大,吸引周边的人也来喝酒跳舞,采访变成了一个大party。

南部非洲,女子成人节的少女红服装(2016年摄)
梁子:比如我在厄立特里亚认识的村妇女主任马迪娜,别人介绍说她是一个寡妇。
当地寡妇地位比较低,不能戴任何首饰。但我跟她接触后,感觉她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人,有光芒,在妇女中有号召力。原来她出生在一个勇敢者的家庭,她爸爸原来做过酋长。
她还给我讲了她叔叔的故事,有一头狮子把他们家骆驼咬死了,叔叔去找狮子报仇。在沙漠中找了三天才找到,他把胳膊缠上厚厚的布,直奔狮子而去,在狮子张大嘴的时候,他的手瞬间以极大的力量捅进了狮子嗓子眼。我听完很震撼,打败狮子的人是真正的英雄啊!马迪娜不歧视外来人,没有占便宜的小心思,她是这个村里最好的女人。

《中国妇女》:我注意到您讲那个叔叔打狮子的故事特别有激情,崇尚英雄跟您生活在军人家庭以及自己当过兵有关系吗?
梁子:有很大关系,我父亲是军人,从不溺爱孩子。1986年我正要从青海省军区调到北京,老山轮战,要扩大新闻队伍,我是摄影记者,就给我爸打电话说我不回北京了,我要上战场。
我爸了解我,说如果你决定了,那我送你两句话:第一做好吃大苦的准备,第二做好牺牲的准备。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样的家庭,怎么能不培养出我这样的人?
前线的摄影女兵就我一个,我拍下了很多战士人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见证过战争的残酷,人就会不一样了。我后来还进了英模报告团,但我从不认为我是英模,那么多战友舍生忘死,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我特别崇尚大无畏、勇敢、豪迈,那是我的审美。
《中国妇女》:这么多年去过多次非洲,您觉得那里的女性状况有变化吗?
梁子:女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上。过去都是包办,现在很多地方能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有的地方女人要生过三个孩子以后才能出来见其他男性,现在改变为生两个孩子或者生一个孩子就能出来……有了互联网以后,女性的就业意识、学习意识都比以前有所增强。

《中国妇女》:您曾说您前十年记录非洲女性,后十年是记录在非洲打拼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在非洲是怎样的?
梁子:我在非洲接触过从事各种职业的中国女性,办学校教中文的,做物流运水泥沙子的,做音乐的,最多的是开商店、开餐厅、办工厂的……中国女性普遍都是奋斗型的,特别励志。
比如马晓梅,西安女子,文化不高,最早被招去马达加斯加做裁缝,后来一点点打拼,在肯尼亚、卢旺达都开了服装厂,自己当了老板。李丫丫本来是贵州师范大学的老师,公派到非洲教中文,后来辞职,自己在桑给巴尔岛上教授中文、带旅游团,她教过的当地学生超过千人,甚至促成将汉语课程纳入岛上的国民教育体系,当地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有中文课程。
《中国妇女》:从一地到另一地,陌生地方陌生人,意味着各种未知。很多人的恐惧都来自未知,为什么您没有这种恐惧?
有的人社恐有的人社牛,我觉得我是牛中之牛,这里和那里不一样,这人和那人不一样,我想知道的东西很多,这就是我的兴奋点。
《中国妇女》:您每年都要出去很久,在家的时间有限,您先生对此怎么看?
《中国妇女》:行走中遇到的最感动和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梁子:感动和恐怖的事情很多,说不上“最”。在莱索托东北部一个叫塔巴姆的村庄,我接触了一位41岁的女艾滋病患者,她死前在地上的垫子上躺了5个月,骨瘦如柴。
临终时,她拉着我的手,我以为她要说“救救我”,或者帮帮她的5个孩子、给她点钱之类的,但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看着外面的天空,十分吃力地蹦出来的英语单词,全是关于大自然的,河流、天空、白云、空气……她在向往着与大自然融合,我特别震惊。当时只带了照相机,她说的话我录不下来,也是因为这件事,我后来去非洲开始带摄像机。
这个人去世那天晚上狂风暴雨,雨打在铁皮房顶上跟子弹打下来似的,哒哒哒响,又没电,我开始害怕,把带的蜡烛一下点了12根。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暗夜中浮现几个黑乎乎湿漉漉的面孔,我吓死了。原来是村民叫我一起去守灵,我没敢去。
但下葬那天我去了,棺材放在一个茅草搭的小黑屋里,人们围着棺材转,和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出来的人表情都很惊惧,我知道一定是尸体的样子很可怕,转到我的时候,我几乎没敢睁眼看。虽然我经历过战场,见过更加恐怖的场景,但那是战友,我们是一个群体在共同面对,内心好似有铜墙铁壁,而那时却感觉难以承受。
《中国妇女》:您在行走中经历过各种危险,比如得过疟疾,陷入过沼泽,遇到过毒蛇……这些生死考验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梁子:2002年5月7号,我本来要去大连电视台参加一个节目,电视台给我买的是晚上8点多的机票,但因为我4月从塞拉利昂回来之后得了挺重的疟疾,持续了一个多月,一直断断续续发烧,那天下午我又发烧了,只好跟电视台的人说去不成了,然后把家里电话线拔了就睡觉了,第二天醒来才知道我原来订的那个航班坠机了。
我很幸运,也慨叹生命之无常。我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行万里路的方式读万卷书,我热爱生命,也接受现实,这让我在面对许多突发灾难事件和危险时,能够保持冷静的判断力和处事的果断性。最重要的是,我拥有一颗坚强的心。我相信,丰富的生命更有力量也更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