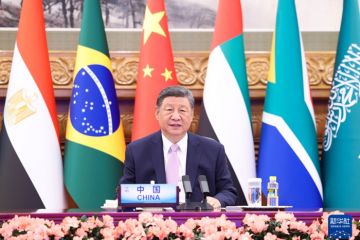映照家国情朗朗秋月

时间过得真快,残暑未消,秋风又起,一年也就过去了三分之二。在古人心中,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风物,也有每个季节的风情。东晋陶渊明的《四时》诗中说:“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秋天的标志性风物是清辉万里的月亮。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首写女性,也写月亮的诗,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意象真美。它不是春天的明媚之美,也不是夏天的浓艳之美,而是专属秋天的素洁之美。素洁在哪里?在月亮。月亮是静夜之中一个皎洁而温柔的存在。诗歌中大凡写月亮,总是给人以素洁的联想。“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如此,“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如此,“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如此,“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还是如此。秋月明,秋月白,以秋月起兴,马上,整个画面都优雅宁静起来。
但这两句诗又不仅仅是素洁,它还宏大。宏大在哪里?在“一片”和“万户”。一片月下,万户捣衣,整座长安城都笼罩在明净的月光下,整座长安城也都沉浸在一片此起彼伏的砧杵声中。月光从天上洒落到地下,捣衣声又从地面直达天上,这“一片”与“万户”背后,是天与地,月与人,光与声的交相辉映,这是多么宏大的场景啊!可这两句诗又不仅宏大,它还柔婉。柔婉在哪里呢?在月下捣衣这个特殊的场景。秋天最典型的女红,就是捣衣了。所谓捣衣,并不是洗衣,而是把衣料放在石砧上用棒槌捶打,让衣料变软,然后才能裁剪制衣。换句话说,捣衣是做衣服的前奏,而秋天,正是赶制冬衣的季节。为什么要在月下捣衣呢?因为捣衣是一件耗时耗力的活计,但并不那么精细,精打细算的主妇们舍不得白天的时间,所以都会选择在晚上,趁着月光来做。这才会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样经典的秋夜女红场景,这个场景是属于女性的,属于月夜的,当然令人觉得柔婉细腻。
“长安一片月”是秋色,“万户捣衣声”是秋声,那接下来呢?“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属于秋天的经典风物,不仅有秋色,秋声,还有那带着凉意的,撩人愁思的飒飒秋风啊。秋风能吹走暑热,吹走落叶,却怎么也吹不尽思妇对玉门关外征夫的绵绵相思之情。这“玉关情”三个字从哪里来?其实早就蕴含在前两句诗里了。望月怀远是中国文学的大主题,起兴既然是“长安一片月”,思妇怎能不想起“隔千里兮共明月”的丈夫?捣衣是制衣的前奏,要做冬衣了,思妇怎能不惦念身在塞外苦寒之地的丈夫?思妇身处长安城中,心却在玉门关外,她眼中看的,是那轮同样高悬在丈夫头上的月亮;她手里捣的,是即将穿在丈夫身上的寒衣。她眼里看的,手里捣的,不都是“玉关情”吗!这情思无时无刻不深藏在心头,此时被恼人的秋风一撩拨,变得更深更浓了,它和秋月,秋声,秋风一起构成秋意,在长安城中低回不已,挥之不去。这情意,是何等深沉绵长啊。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写景,景中含情;“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写情,情中有景。场景也从天上写到地下,又从长安城一直跨到玉门关。写得情景交融,浑然天成。按照王夫之《唐诗评选》的说法,“是天壤间生成好句,被太白拾得”,所以,有诗评家说,到这里就够了。到底够了没有呢?李白觉得还没够,他又加了两句:“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什么时候才能平定胡虏,让我的良人不再远征呢!这是什么?这是思妇的深沉喟叹,也是属于她们的边塞诗啊。说到唐朝的边塞诗,我们总容易想起那些壮怀激烈的诗句,其实,边塞的情怀,不止有“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的壮志;不止有“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的激昂;还有“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惨痛;以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凄艳。没有前者,唐诗就没有了风骨;但是,没有后者,唐诗也就没有了良心。
那么,“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属于哪一种呢?它又和我们之前说的都不一样。它当然不是好战的,但也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反战,它表达的,是一种更加温柔敦厚的感情:胡虏是要平定的,那是国家的大义;良人也是要回家的,那是个人的私情。这长安的思妇,既顾大局,又重情义,所以才会在这秋风凉,秋月明的秋夜之中,发出这样的喟叹:“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既然如此,这两句诗有没有必要?太有必要了,它把诗的境界一下子升华了。升华成一片既顾念小家,也体恤大家的深厚情义。拥有这般情义的,不是秦罗敷、杨贵妃那样著名的美女,而是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的长安思妇,她们朴实无华,她们情深义重,她们与国休戚。她们代表着人类普遍的生活和情感,像月光一样,清辉万里,抚慰着千古人心。
中国古代的性别分工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妇女被限制在家门以里,主中馈,勤女红,把一生贡献给家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完全脱离社会。就像这首诗里讲的长安思妇,虽然可能终其一生都未曾出过长安城门,但是,她们手中的寒衣,她们心中的牵挂却飞跃万水千山。她们和她们的良人,一起守望着大唐的边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十五的月亮》曾经唱彻大江南北。歌词里那位“守在婴儿的摇篮前”的军嫂,和李白笔下捣衣的思妇,可谓千载同心。
时光悠悠,秋风又吹拂了一千多年。如今的女性早就不在月下捣衣了。走进现代的我们,是工人、是农民、是白领,是企业家,是教师,是医生……但我相信,这篇《子夜吴歌》中传达出来的美与情也同样属于我们,属于所有时代为了小家幸福、为了国家安宁而认真生活的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