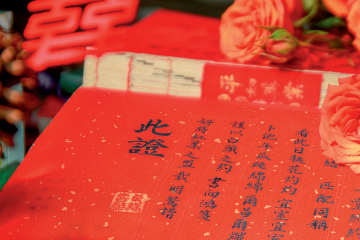曾经牵着父亲的衣襟

中午读柴静的《看见》,她写幼年读书的情景: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
这段话,让我想起了自己儿时读书的光景。
读小学时,一家人随父亲住在河北临清的一个小乡村里。冬夜冷而静,偶尔有几声狗叫。朦胧中听到父亲在唤:上学了!我起身,透过窗户向外看,似乎到处都蒙了霜,泛着银色的光。简单地洗把脸,将一个凉馒头塞进书包,便出了门。星星眨着眼,月亮清冷地透着寒气。坑坑洼洼的坡地上,竖着一些光秃秃的树,在月光下拉着长长的影子。沿途的小桥孤零零地横在河面,河水冻成冰,成了一条银色的亮带。马路上,几辆马车在歇脚,旁边拢着一堆火,车夫裹着破旧的大衣在火边偎着,半倚半靠,无精打采地垂着头,看背着书包的我走过,歪起头投过来疑惑的一瞥。学校在马路边上,简易的铁栅栏门关得紧紧的。我站在门口,哈着冻得生疼的手,摁着书包里的馒头,不知吃还是不吃。几乎没有过往的车辆,更没有早起的行人。又等了不知多久,直到脚冻得生疼,才隐约望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竟是父亲。“回去吧,看错表了,正半夜呢。”他喊。那会儿,说不出是委屈还是感动,泪一下就湿了眼睛。拽着他的衣襟,深一脚浅一脚地又走回家去,一路上父女俩都不说话。快到家时,父亲才问:“冷不冷?”
那是幼年不多的一次与父亲依偎。自从母亲走后,父亲也似乎变得隔膜起来。刚过十岁,我就开始挑水,半桶,晃晃悠悠,踉踉跄跄,肩膀硌得生疼。父亲见了,或是“唔”一声,或是抬眼看一下,但从不接过去,我只好努着力气,费劲地将水倒进缸里。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父亲只保持着道义上的亲情。直到他生病,我去医院探望,他浑浊的眼睛突然发亮,指着我,惊喜地叫:看!看!他叫不出我的名字,有点失忆,有点口吃。父亲孩子似的模样,让我的心忽然有了酸痛感。
似乎是秋天的树,叶不停地落,直到变成一棵光秃秃的树干。人到中年,慢慢看开了一些事,再回忆父亲,渐渐释怀。那时的他,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的负累,让他变得麻木,淡漠。或许,他那时能给予我的,只有那么多了。
父亲日复一日地老了,每次回家,看到的都是他既期待又迷茫的眼神。前段时间打电话,得知父亲在卫生间跌了一跤,急忙询问情况,谁知他只说了一个 “疼” 字便不再言语。当时正出差,心里久久不安。
农历八月十四是父亲的八十岁生日,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原计划长假回去的,但那会儿没有犹豫,当即决定回去为父亲祝寿,并答应父亲,“十一”期间我会再回去看他。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连说了两个“好”,终于满足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