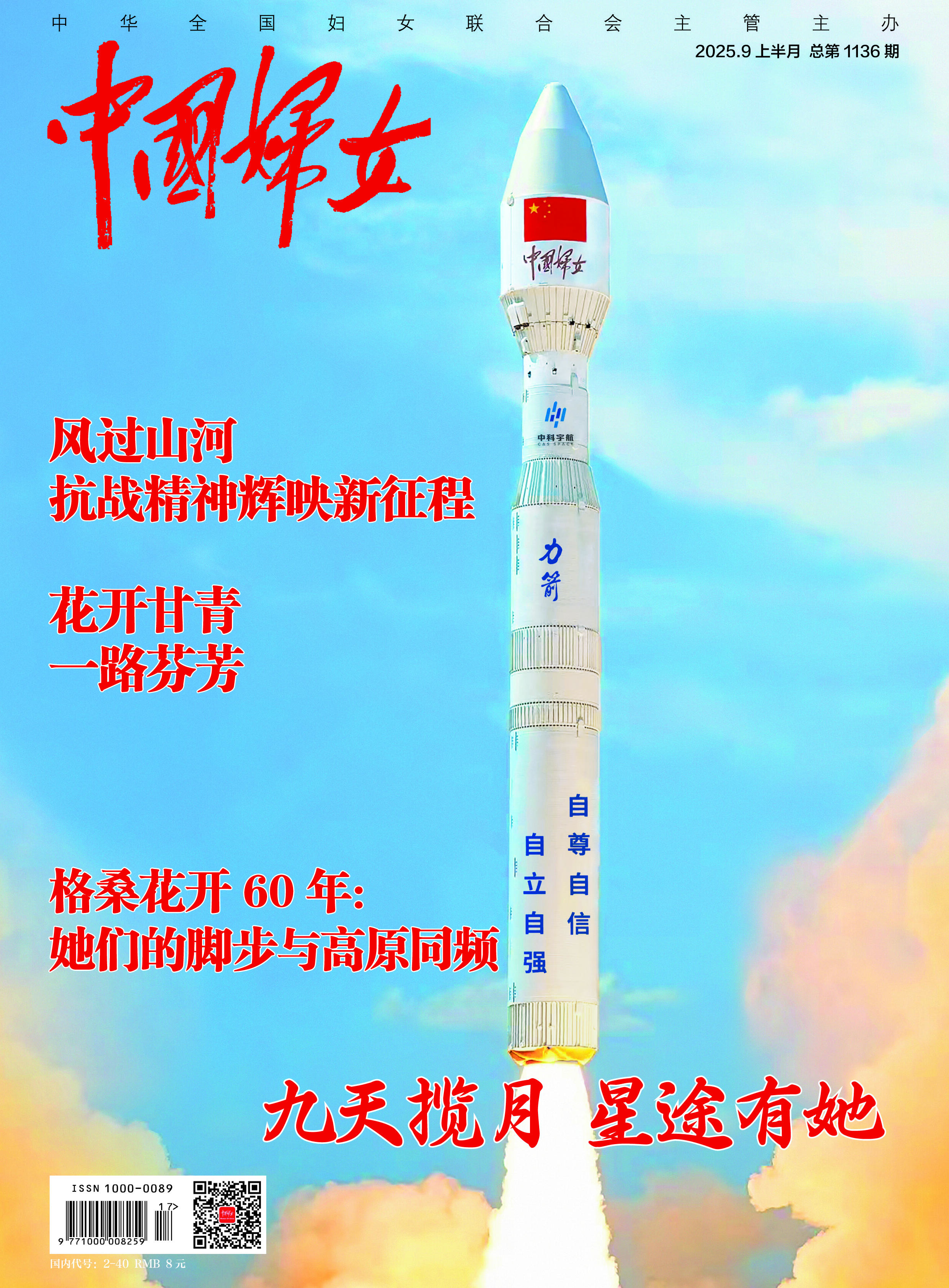妈妈,你去了哪里?
来源:中国妇女网作者:徐鲁
婚姻与家庭
2013-01-31 10:42:00
在妈妈生病的那些漫长和艰难的日子里,我幼小的心中一直怀着这样一个信念:苦菜花开了的时候,妈妈的病一定就会好起来的!

徐鲁,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海豚传媒副总经理。
妈妈做的萩花鸡蛋饼
从日本诗人小林一茶的俳句里读到一个句子:“小鹿吃过的萩花呀!”我的心顿时好像被揪了一下的难受,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我没有亲眼见过小鹿吃过的萩花,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养过一只灰色的小羊,亲眼看见过小羊吃着萩花的样子。
小时候,我还吃过妈妈给我做的鸡蛋萩花薄饼。
那时候因为家里穷,经常吃不饱饭,我的身体很虚弱,时常生病。每当生病的时候,妈妈就会从积攒了许久的鸡蛋坛子里拿出两三只来,给我做荷包蛋吃。我知道,那些鸡蛋是妈妈准备攒够了数就拿到供销社去卖掉,给全家换回油盐和火柴等日用品的,平时谁也舍不得吃。
有时候,妈妈也把一些味道很苦的草药,例如蒲公英、柴胡的根茎,捣碎了,搅拌上一两个鸡蛋,煎出薄薄的鸡蛋饼给我吃。我记得小时候吃过的鸡蛋饼里,最好吃的是槐花饼和萩花饼,因为它们一点也不苦。有一种牛蒡根,苦得难以下咽。可是因为是用珍贵的鸡蛋煎成的,我一点也不敢抛撒,即使再苦再难下咽,也会吃得干干净净的。
萩花,又叫胡枝子、野花生。在白露过后的晚秋时节,在凉凉的秋风里,枝叶细长、花苞微小的萩花,默默地、静静地开放了。淡蓝色系的苞形花串,看上去很美,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就像在为秋天画上最后的句号,美得让人心疼。萩花是我在童年时代里就很喜欢的一种小野花。秋深的时候,萩花有的开成淡蓝色,有的开成淡紫色。细细的枝茎好像冻得通红了,弱小的花冠好像冻得苍白了。是那样的含蓄无声,又是那样的安静。
它们当然也要化作春泥。但是它们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凄凉,而是那么静美,那么安详,又那么意味深长。似乎还在守望着最后一丝孤寂,最后一丝馨香,然后才一点一点地、慢慢地消瘦和谢落,就像那些产后的小母亲失血的微笑。
不知道为什么,小小的萩花,和同样是在晚秋里绽开的苦荞花一样,总会让我想到故乡那些苦命的小女子。
不知不觉,妈妈过世已经四十年了。
妈妈不在了,我从此再也没有吃过薄薄的鸡蛋萩花饼。
小学时代的奖状
少年时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记住了这样一个细节:卓娅和舒拉的妈妈在回忆第一次送孩子们去上学的情景时说,无论是哪位妈妈,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都会是她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美好的日子,所有的妈妈一定都记着那一天。
我上学念书那年已经八岁,可我实在不记得妈妈送我到学校那天的情景了。如果妈妈现在还活着,我一定要问问清楚的,我相信妈妈一定会记得。我努力地想啊,唯一能够想起的是,当时我有一个很漂亮的花书包,那是妈妈用从街坊邻居家讨来的各色花布边角拼做而成的。书包里装着一块崭新的带小木框的石板,另有一小捆白色的细石笔——那是妈妈用卖鸡蛋的钱从集镇上为我买回来的。我的一套崭新的“学生蓝”制服的前襟上,有妈妈为我别上的一块蓝手绢。
我想,当妈妈牵着我的手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她肯定是又自豪又依依不舍的。她或许正在担心,今天,她把自己心爱的儿子交给了世界,明天,这个世界将会还她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而我的神态,大概是又得意又有些惶恐的吧?
我在家乡小学念书的五年时间里,自始至终被每一位老师及村里的大爷、婶婶们视为勤奋用功、好学上进的“好孩子”。我还是我们那一级的第一位由老校长亲自给佩戴上了红领巾的学生,好几次代表学校出席了学区的“三好”学生代表大会。单是我每年放寒假时领回来的奖状,就足令许多家长和小伙伴钦羡不已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领到的奖品,除了一张奖状外,还有一张最新的毛主席像和一个漂亮的硬面笔记本,我把它们交到妈妈手上时,妈妈高兴得流着泪把我紧紧地拥进怀里。妈妈在村里一向善良、贤淑和要强,当时她把我看了又看,抚摸了又抚摸,说我是一个争气的孩子。
那些奖状,妈妈总在每年过年的前几天,仔细地把它们钉到墙壁上,旁边配上别的年画。正月间,凡来走亲戚的人,尤其是一些长辈,都会看到它们,而且都会啧啧称赞我有出息。妈妈从这些长辈的称赞里,默默地感到了极大的安慰。可以想象,在妈妈的心中,一定浮现着我的灿烂的前程。
过了正月十五,妈妈又会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奖状一一取下来,用旧报纸卷好,放进我们家那个大红漆的木箱子里,第二年年关时再拿出来。
妈妈不在了,我的童年时代也结束了。
后来我离开了故乡,去远方寻找我金色的前程。那些留在老家的小学时代的奖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在哪里了。
我想起了一首英文歌曲里唱的:
“面对流逝的往事,最坚强的人也会呜咽……”
风雪中的小路
在我们村里,妈妈以自己的勤劳、善良、能干赢得了长辈们的夸赞和晚辈们的尊敬。对于村里的孤苦饥寒,妈妈宁肯自己家里人少吃一口、少用一点,也要尽力周济别人,热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可是一场大病让妈妈突然倒下,最终也没有医治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妈妈病重期间,我正是十二三岁的年龄,有两三年,几乎是每天一放了学,就要来回奔跑在从我们村到十几里远的杨戈庄的那条崎岖的山野小道上,去为妈妈求医抓药。杨戈庄上的杨大爷,人们都称他“杨善人”,他家里有个在当地极有名望的小药铺。
到杨戈庄去,要经过一条又窄又险的山路。我记得,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我揣着新药方,抱着一只老母鸡,踩着没膝深的大雪,走着走着,只觉得四周白茫茫、明晃晃的一片,找不着路了。一不留意,我一脚踩进了深沟里。幸亏有厚厚的积雪托着我轻薄的身子。摸索着爬起来,拍拍满身的雪花,紧了紧靴子带,继续赶路。
荒野之上,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等到终于摸到了杨大爷家门口时,人家早已关门睡下了。
“杨大爷,杨大爷,开开门,是我呀!”
这半夜的叫门声,惹得胡同里外的狗儿汪汪直叫。
杨大爷开了门,见我满身雪花、满头大汗,一把把我拉进了屋里,心疼地说道:“孩子,都后半夜了,你是怎么走来的?可不要把小身子骨糟蹋了哪!”
杨大爷让我脱下靴子,偎在热炕上暖和着双脚,然后麻利地为我配好了药。听说他的药铺最高的一格抽屉里的药,都是祖传的,而且都很贵重。
我告诉杨大爷说:“大爷,家里没有现钱了,这只老母鸡就当药钱吧。每次都让您费心……”
杨大爷说:“孩子,治病要紧,治病要紧。这老母鸡大爷可不能收,我先记上账就行了。”
“大爷,您也得过日子呢!”我放下老母鸡,拿起药包就往回赶路。
往家里赶的路上,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说:“老天爷啊,求求啦,快让我妈妈的病早些好起来吧!求求啦!”
那时候,我的心里总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也许吃了这一剂药,妈妈的病就会好起来的吧?是的,会好起来的!妈妈的病好了,我们往后的日子也就会好起来的。常常是一边走着一边想,不知不觉,十几里的夜路就走完了。远远地可以望见黑魆魆的村子了。那寂静得没有一点声息的村子,连一星灯火也看不见,只有野外的风雪在号叫着,呜呜地从这面山吹到那面山上去……
大风雪中的一条模糊的小路,牵引着我,气喘咻咻地回到了家门。全家人看见我抓回的新药,又像看到了新的希望。爸爸会连夜小心翼翼地把药煎上。
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疲乏得连衣裳都没有力气脱了。可是,刚歪到炕上打了个盹儿,邻家的鸡已经开始鸣叫了。我知道,那等待着我的是另一条上学的小路。
我记得,我妈妈去世前最想吃的东西,是苦苦菜!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苦苦菜还在大雪下埋着。在妈妈生病的那些漫长和艰难的日子里,我幼小的心中一直怀着这样一个信念:苦菜花开了的时候,妈妈的病一定就会好起来的!为此,我几乎是天天一个人跑到村外,在大雪天里,在荒凉的山野上,仔细地寻找着、挖刨着妈妈所想念的苦苦菜。
终于有一天,我在一块避风处挖到了一簇刚刚露出小芽的苦苦菜根。我欣喜地捧着菜根往家里跑。但妈妈没能看到和吃到我挖回来的苦苦菜根,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苦苦菜没能挽救妈妈的生命,她含着一生的辛苦,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妈妈,你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