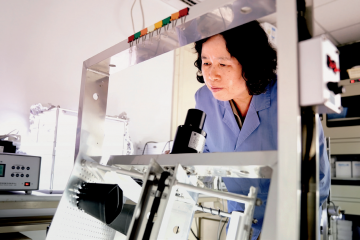我想画出帕米尔的灵魂

燕娅娅
中国民族书画院画家。多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作品被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印度、土耳其、日本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画廊、美术馆、个人收藏。
从1987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间,我几乎年年都上帕米尔。这个亚洲腹地的神秘高原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的画倾注了我毕生的情爱,我的生命和灵魂已经融入了帕米尔。它让我魂牵梦绕,每次上高原就像回家,是去团聚,是去过节,是去了一段相思情。
帕米尔,我来了!
1987年,我在中央美院上大四,为了交毕业作品,我只身来到新疆喀什。我在艾提尕尔广场写生时,有一个围观的人建议我去塔什库尔干县,说那才是画画的好地方。
尽管对帕米尔一无所知,年轻气盛的我真就拦了一辆大货车上山了。当大车走在悬崖峭壁间狭窄的公路上时,我有点后悔了。可偏偏大货车坏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野里。驾驶员让我看车,他要去几十公里外找配件。
尽管是夏天,但天黑后的高原还是寒风刺骨。就要冻成冰棍时,我发现驾驶室还有半包火柴。于是我找来报纸揉成团,想用它去点荒野里拾来的梭梭草。因为风大,划着的火柴一次次被吹灭,就剩最后几根火柴了!我急了,干脆把报纸塞在衣服里,点着了报纸,然后又点着了梭梭草。在噼里啪啦的热浪中,我似乎产生了幻觉,觉得周围有异样的声音,四周都闪烁着幽幽的绿光。当时我就一个想法,火不能灭。直到天快亮时,驾驶员才出现在我眼前。他说:“真的对不起,我没办法赶回来。昨夜,你没见到什么吗?”我摇头。他说,他过来时,在周围看到了不少羚羊的粪便,这里有句老话,羚羊到哪里,狼就跟到哪里。看到这么多羚羊的粪便和野狼的足迹,一定是一个大狼群来过。我一听,当即瘫软在地。

作品《家在高原》
到塔什库尔干县城时,天已经黑了。我在当时唯一的一个条件十分简陋的旅社住下来。天刚蒙蒙亮,我就奔了出去。登上石头城,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太阳正缓缓升起,一片片似乎伸手就能摸到的云彩被染成深浅不同的红色。远处是白色的雪山,近处是绿色的草滩,滩上的毡房炊烟袅袅。毡房里“飘出”穿着红色衣裙、披着长长红纱巾的“仙女”,牛羊悠闲地游荡在草地和溪水间……天亮了,天空湛蓝,白云朵朵。
身置仙境,我哭了,就是历经再多的苦难都值得啊。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帕米尔,我来了!”
于是,我疯狂写生,带着厚厚一沓草稿回了学校。
但狂喜之后我陷入沉思,帕米尔不该只是美,我需要找到它美的灵魂。于是,我静下心来,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帕米尔和塔吉克人的文章。
她叫我妈妈,我要带她走
第二次到塔什库尔干县是三年以后。第一天,我独坐在那片草滩,饶有兴趣地看在草滩上踢足球的男孩们。孩子们友好地给我传球。其实,那个足球就是一个破了的足球皮,里面塞了填充物,再缝合起来。我和孩子们几乎玩了一天,我们之间除了眼神的交流就是笑。傍晚,一个大孩子说了几句什么,小伙伴们立刻在我面前站成一队,然后开始一个个给我表演翻跟头。我一下明白了,他们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谢谢我陪他们玩。我哭了,跑过去心疼地抱住他们试图阻止——毕竟是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强烈的运动使人消耗太大。

作品《小西仁古丽》
从此,塔吉克孩子让我情有独钟。每次上山,我都尽量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干什么我就跟着干什么。到了2003年,我把我画的一百多个塔吉克孩子的油画作品带到了中国美术馆。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故事,一双双孩子的眼睛,折射着不同的感受和色彩。
2005年,在经过了非常艰难的一段路程后,我来到距离县城一天路程的瓦恰乡。我问陪同的武警战士,当地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孩子。他们说有一个小女孩很可怜,没有妈妈,父亲靠政府救济。我要求去看看。
当时同行的有姐姐燕娜娜和五位战士。远远看到从石头房里走出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定睛看着这群陌生人,突然挣脱父亲的手向我们跑来。她绕过前面的武警战士和姐姐,直奔向我,嘴里竟喊着:“妈妈!妈妈!”
尽管有些突然,但我能做的就是蹲下来,张开双臂。女孩毫不犹豫地扑进我的怀里,我抱着她,哭成一团。我深信这是缘分。
在那间一贫如洗的石头屋里,我看到地上几个长了芽的土豆和存留在锅底的清淡如水的奶茶。我擦干眼泪说:“她叫我妈妈,我要带她走。”姐姐说:“你可想好,走了这一步,就要走一辈子。”我坚定地点头。
这孩子叫阿合夏,5岁。8个月的时候妈妈走了,爸爸塔加木力将她艰难带大。塔加木力听翻译说了我的意图,眼里充满感激和信任,没有犹豫就点头同意,他深知女儿跟着我比跟他好。
随后,我这个妈妈带着她去兰州,学汉语,上幼儿园……在塔什库尔干县边防武警总队的协助下,她拿到了去丽江上学的名额。我辗转在丽江、北京、塔什库尔干之间,每年都给她的父亲汇报她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几年后,我发现出了问题。当阿合夏能自如使用汉语的时候,她却遗忘了母语,甚至忘了父亲的长相。这让我很纠结,怎么能忘了根呢?这可不是真正的帮助。于是,我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妈妈、姐姐商量决定,送孩子回塔什库尔干县上学。让她拾回母语、拾回应该属于她的一切后,再接她出来学习。
今年夏天,当阿合夏从依稀的记忆中找回了爸爸,热情地拥抱爸爸的那一刻,我的心放下了。
她们一个个都成为我的画中人
奶奶坐在山坡上等我
每次见到泥沙汗奶奶,她都是站在山坡上慈祥地望着我。她总穿一身黑色长袍,戴白色头巾,一根长辫子从一侧肩膀顺过来,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泥沙汗奶奶在我心里就像一个女神。
2005年冬天,家父去世,我的悲伤无以释怀,于是,又想到了帕米尔。那是我第一次冬季上山。路上,我想起年事已高的奶奶,就有了要为奶奶画一幅画的愿望,但是,之前我并没有画过老人。我想,大雪皑皑,奶奶还会站在山坡上等我吗?然而,快到的时候我抬头一望,不由惊呆了,奶奶正站在山坡上望着我呢。
我百感交集,流着眼泪奔向她,奶奶也一步步走下山坡迎向我。我们拥抱在一起,奶奶为我擦去眼泪,深深地亲吻我的额头,无比怜爱地看着我。就在这一刻,我知道奶奶该怎么画了。我比画着给奶奶承诺:“奶奶,你等着我,我要给你画像!”
带着灵感我冲下山,飞回画室,20天没有出门,《泥沙汗奶奶》一气呵成,所有看到画像的人都被奶奶那一脸的慈祥感动了。我为画像拍了照片,装裱起来,又买机票去了喀什。
这回,奶奶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新衣服,戴着新围巾正坐在石头上张望。我跑过去拿画像给她看。奶奶看着笑出了眼泪,拿照片的手颤抖了。她儿子说:“我还奇怪,老太太今天一定要穿新衣服,说有远方客人要来。我说这大冬天的,怎么会有客人。是你来了啊!”
是心有灵犀吗?我告诉奶奶,我要拿着这幅画去香港讲故事,我要带着奶奶去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认识奶奶。不知奶奶听懂了没有,但奶奶高兴地点头。
我带着奶奶去了香港,去了东南亚,还去了七八次中国美术馆……她的故事感动了太多的人。这幅作品已不再是绘画技术的展示,而是民族内涵、情意的展示。
他们是我心里最爱的人,我充满感情地画他们,他们有着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人性美,质朴、善良、勤劳……